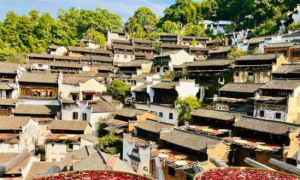广西一男子因幻想邻居“作法”害自己,持枪射杀一对夫妇,一审被判死缓后检察院以“量刑不当”提出抗诉,二审开庭在即。
2023年12月4日上午,广西来宾市一声枪响,打破了一个普通村庄的宁静。26岁的何某某携带两支自制改装射钉枪,闯入邻居家中,对准两位六旬老人头部扣下扳机。他后来向警方供述,杀人动机是长期认为对方“在菜地作法摆阵”,导致他严重失眠、“深受其害”。

2025年3月,来宾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何某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认定,何某某“作案时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人”并“具有自首情节”。
然而,判决并未终结这场悲剧。
2025年4月16日,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提出抗诉,认为“量刑明显不当”,应当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2025年9月23日,该案二审即将开庭。
一、菜地、邻居与“作法”:一场虚幻的迫害妄想
案发当天上午10点左右,何某某携带两支已上弹的改装射钉枪,推开何某本与黄某玉家那扇并未紧闭的门。
没有任何争执,也没有预警。
他直接朝两位老人头部开枪,随后离开。
警方后来调查证实,何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
他长期坚信邻居夫妇在他家附近的菜地里“施法”,导致他失眠、身体不适、诸事不顺。
事实上,那只是两位老人日常种菜、除草的地方。
两家人之间仅一墙之隔,本是邻里守望的距离,却成了妄想滋生的土壤。
在何某某的认知中,那片菜地不再是菜地,而是“害他”的法场。
二、弹痕仍在,人已不在:一个家庭无声的破碎
案发后,儿子何先生再不愿回到老屋。
“看了伤心,”他说。
那栋父母居住多年的房子里,门框上至今仍清晰留着射钉枪的弹痕。
它们成为那个早晨无法抹去的证据,也是一个家庭轰然倒塌的印记。
何先生怎么也无法理解,父母勤恳善良一辈子,平日种菜除草、安分守己,最终却因邻居的“幻想”丧命。
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一审判决并未判处凶手死刑立即执行。
三、“限定责任能力”与“自首”:生与死之间的法律争议
一审法院作出死缓判决,主要基于两个法定从宽情节:
- 司法鉴定显示,何某某作案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属“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 作案后,何某某没有逃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依法构成自首。
但检察院指出,何某某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直接射击头部,明显追求被害人死亡”;
作案目的极其主观——“经预谋准备,非法制造枪支,主动行凶”;
结果极其严重——“造成两命死亡”。
即便存在部分从轻情节,仍不足以减轻其罪责。
检察院认为,何某某“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抗诉与期盼:司法如何回应一场人伦悲剧
2025年4月,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正式提出抗诉。
这意味着,法律系统内部对量刑产生了重大分歧,也意味着被害人家庭迎来了唯一一线希望。
9月23日,二审开庭在即。
何先生和家人等待着,他们也希望司法系统能够给出一个回应:
当一场凶杀源自“幻想”,当两个生命因“妄想”而逝,法律究竟该如何衡量生命的重量?
五、悲剧之外:精神障碍≠免责金牌
此案也再次引发一个沉重议题:精神病患犯罪,司法该如何平衡“惩戒”与“救赎”?
我国刑法规定,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但这并不意味着“患病即免责”。
特别是当行为人明知自身行为违法、仍有计划地实施极端暴力犯罪时,司法不能忽视对公众安全的保护与社会正义的维护。
检察院的抗诉,正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态度:
刑罚的轻重,必须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称。
2025年9月23日,广西高院。
法庭之上,将有一场关于生死、责任、精神病与刑罚的激烈交锋。
法庭之外,两个家庭,都在等待一个答案。
而那条分隔两家、曾种满蔬菜的围墙,依然立在那里。
只是墙的一边,再没有人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