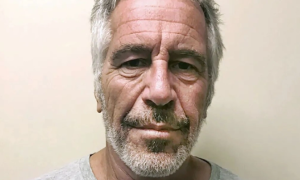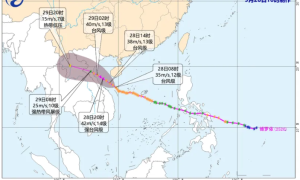河南的一个小村庄,走出了中国影视行业七成的灯光师,他们用朴实的光影手艺,点亮了屏幕里的万千世界。
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附近,一座现代化的竖屏电影基地——“聚美空港”悄然运转。这里没有华丽的布景,也没有奢华的装潢,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贴着“女总裁家”“豪门客厅”标签的简易样板间。就在这里,一批又一批“霸总”“千金”的故事被流水线般生产出来,输送到成千上万用户的手机屏幕上。

但真正支撑起这个光影世界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而是一群常常被忽略的“幕后英雄”——灯光师。他们中,有七成来自河南,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又来自同一个并不起眼的小村庄:许昌市鄢陵县张桥镇张北村。
一、“灯爷”的江湖
“灯光师!我的灯光师!”薛之谦曾在乌鲁木齐的演唱会上,用带着河南口音的呼喊向幕后致敬。这一幕被无数网友转发,也让“河南灯光师”这一群体意外“出圈”。
事实上,他们早已是中国影视工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从横店到重庆,从电影大片到短剧流水线,只要有打光的地方,就很难缺少河南口音。他们可能不善言辞,衣着朴素,甚至教育程度不高,但他们手中掌控的光,却能决定一部作品的质感、一个人物的情绪,甚至一段故事的说服力。
老一代的“灯爷”侯登高,从1992年就来到北京。那时他还在工地搬砖,每天挣8块钱。听说在剧组做群演一天能挣20块,他想都没想就挤进了北漂的影视大军。“一开始是做群众演员,后来灯光组缺小工,我们就去扛灯布線——没想到,这一扛就是三十年。”
如今,他已成为很多年轻灯光师口中的“侯老师”。但他依然愿意在短剧剧组里做灯光助理,跟着比他小二十岁的王浩雨一起干活。“他是指导,我是助理,得听他的。”侯登高笑着说,眼神里却没有丝毫委屈,只有一片包容与从容。
二、一个村庄,半壁江山
如果你跟随灯光师的足迹,从北京的横桥村走到河南的张北村,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走到哪儿,灯光师的名字总绕不开那几个姓氏——王、曹、邢、孙……他们彼此之间不是亲戚,就是邻居。
“这一行,靠的是信任和介绍。”侯登高说道。灯光师接活的方式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乡土逻辑:有活儿先找老师傅,老师傅没空,就找跟过他多年的助理;自己接不过来的项目,也会顺手介绍给老乡。“大家都是张北村出来的,知根知底,靠谱。”
这种“同乡同业”的模式,不仅构建了一张庞大的资源网络,也成为无数河南家庭改变命运的契机。
1997年,灯光师邢建伟在《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担任灯光工作,日薪突破两百元——相当于如今的一线白领收入。自那时起,“灯光村”的名声逐渐打响。
就连大导演陈凯歌在拍摄《荆轲刺秦王》时,也曾一度想不用河南灯光师。结果连续换了八批人,来的却还都是河南老乡。最后陈导也笑了:“河南的就河南的吧!”
他们凭什么征服了整个行业?
三、光,是农民的另一种语言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没有光,哪来的影?”来自横桥村的钱师傅(化名)语气斩钉截铁。他曾参与过《戏说乾隆》的拍摄,是行业里最早一批从河南走出来的“灯爷”之一。
他们没有科班背景,很多人甚至只有小学文化,但他们懂得“悟”。
“学校教的是术语,我们靠的是手感、眼力和脑子。”钱师傅不无自豪地说,“有些外国导演说的术语连翻译都听不懂,但我看他比划一下,光该怎么打,我心里就全明白了。”
真正的好光,是看不见的光。
年轻的王浩雨最佩服他的叔叔王存之,后者曾担任《唐人街探案》《乘风破浪》的灯光指导。“他打出来的光就像没打一样,自然、舒服,但你不知道他在外面用了多少灯、多少心思。”
光,可以制造年代感,也可以渲染情绪;可以突出演员的轮廓,也可以隐藏场景的缺陷。正如灯光师曹松在凭借《小巷人家》获奖时所说的:“斑驳墙面的侧逆光,搪瓷杯上的高光点,煤炉旁氤氲的柔光……这些设计让记忆有了可视的质感。”
四、短剧时代:活下去,还是追光?
如今的影视行业已天翻地覆。大制作电影减少,广告拍摄回款困难,取而代之的是短剧的狂飙突进——十天拍完、一天十集、迅速回本。有人视之为救命稻草,有人则嗤之以鼻。
“多亏了短剧,影视寒冬里我们还有饭吃。”侯登高坦诚地说。为了生活,他愿意俯下身来,去做那些“光一开、机器一架”就开拍的速成项目。
但钱师傅却直言:“短剧那叫光吗?那是照明!”在他看来,灯光是一门艺术,不是流水线作业。“光是一部电影的灵魂啊”,他引用当年八一厂老师傅的话,语气中有些唏嘘。
或许没有谁对谁错,这只是两代灯光师面对时代浪潮的不同选择。一个是为了生存,一个是为了尊严;一个看向地面,一个仍仰望星空。
五、二代灯爷:还会继续追光吗?
如今,越来越多的“灯二代”也开始加入这个行业。
王浩雨,1998年出生,却已有十年灯光经验;钱师傅的儿子2003年出生,如今也已干了六七年。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为了一天20块钱挤破头皮,而是因为“觉得好玩”“喜欢跑组”“不想一年365天待在同一个地方”。
但他们也清楚这行的不易:日夜颠倒、居无定所、没有社保、活接不稳。侯登高就坚决不让自己的小儿子再干这行:“太苦了。”
能熬出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在年轻时拼命赚钱,年纪大了就回到鄢陵老家,开个小店,过上安稳日子。比如拍过《赤壁》的灯光师曹彦峰,如今就在老家卖卤肉。
六、光仍亮着
那天在郑州的竖屏基地,我们见到收工后的王浩雨。他摇下车窗,露出一张年轻而疲惫的脸,笑着问:“撸个串,喝点酒不喝?”
那一刻,他不像一个“灯爷”,更像一个爱玩爱闹的大男孩。但他身后,是满满一车的灯光器材,是他必须负责清点、运送、守护的“家当”。
2025年,影视行业早已褪去光环,灯光师也不再是“暴富”的代名词。但他们依然选择扛起灯架、拉起电缆,在每一个需要光的角落默默站立。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有戏要拍,有光要打——
就总需要一群河南人,用最朴实的方式,点亮最梦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