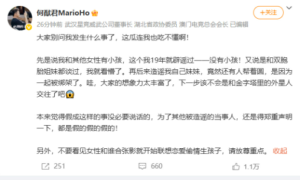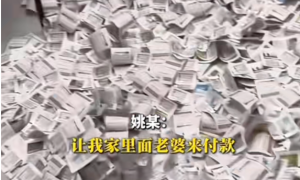“思诺思案”发回重审暴露精神药品管控与司法裁量的深层矛盾,患者转售剩余处方药被控贩毒引发对法律刚性与个案正义的深刻反思。
2025年7月25日,浙江嘉兴中院的一纸裁定书,将”00后女孩网售5盒思诺思被判贩毒案”发回重审。这起看似简单的案件,背后却牵动着司法实践、药品管控与公众认知的多重张力。当22岁的马琳琳因出售自用剩余的思诺思(酒石酸唑吡坦片)获刑七个月时,她或许未曾想到,自己会成为审视我国精神药品管理制度与刑法适用边界的典型案例。这起案件的波折历程,折射出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鸿沟。

一、思诺思的双重身份:从安眠药到”毒品”的法律认定
思诺思作为唑吡坦类镇静催眠药,在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被列为第二类管制药品。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和《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向贩毒、吸毒人员销售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无论主观是否明知,均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这种严格责任认定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具有威慑力,但当适用于普通患者时却可能产生严苛后果。
马琳琳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法律认知的落差。医学专家指出,思诺思与普通民众认知中的”毒品”存在本质区别——它不具有海洛因等毒品的欣快感,临床使用成瘾率仅约3%。北京安定医院药学部主任张莹表示:”许多患者根本不知道这类处方药的法律属性,他们只当是普通安眠药。”这种认知鸿沟在二审中成为辩护重点,律师廖建勋强调:”当事人作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出售剩余药品的行为更接近处置闲置物品,而非毒品交易。”
二、举报人动机迷局:陷阱取证与司法伦理的争议
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它源于买家董某的主动举报。证据显示,这位有吸毒前科的举报人在交易中明确提及药品”有瘾”,却在收货后立即联系警方。这种操作在法律界引发”陷阱取证”的质疑。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曲新久指出:”如果侦查机关利用特定人员引诱本无犯罪意图的人实施’犯罪’,可能涉及刑事诉讼法禁止的诱骗性侦查。”
更值得玩味的是量刑差异。对比类案,2024年江苏某男子通过网络贩卖思诺思200余盒获刑一年,而马琳琳仅出售5盒却被建议同等量刑。这种不均衡暴露出基层司法对《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条款的适用僵化。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当机械适用法律可能导致明显不公时,法官应当发挥司法裁量权,考虑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的实质性判断。”
三、类案不同判的困境:精神药品管控的司法实践图谱
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三年涉及思诺思的贩毒案件中,75%的被告为医疗行业从业者或患者家属,但量刑差异显著。某三甲医院护士因转售20盒思诺思给同事获刑八个月,而某药店老板违规销售50盒却仅处罚金。这种混乱源于对”毒品”与”药品”双重属性的认知分歧。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法律解释的滞后。2007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将管制药品分为三类,但未区分临床使用与毒品滥用的监管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时延安建议:”对精神药品犯罪应建立’双重故意’认定标准,即既要证明行为人明知是管制药品,又要证明其明知购买者将用于非法用途。”
四、制度改良的路径探索:从机械司法到实质正义
马琳琳案发回重审释放出司法系统自我修正的信号。借鉴国外经验,美国《管制物质法》对处方药转售区分”明知用途”;德国则设立”微量不诉”原则,对非营利性转让少量药品免于刑事处罚。这些制度设计为我国提供了参照。
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完善管控体系。建议构建”三阶处置”模式:对医疗从业者故意违规从严打击;对患者偶发转让适用行政处罚;建立官方剩余药品回收渠道。国家药监局正在推行的”智慧药监”系统,可通过区块链技术追溯每一片管制药品的流向,从技术上预防类似事件。
这起案件的价值已超越个案本身,它迫使我们在打击毒品犯罪与保障合理用药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一位年轻患者因处置自用剩余药品而背上”毒贩”罪名时,我们有必要反思:法律的刚性不应成为碾压常识的巨石,而应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天平。正如二审裁定所暗示的,在严格执法与人文关怀之间,司法应当找到更符合实质正义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