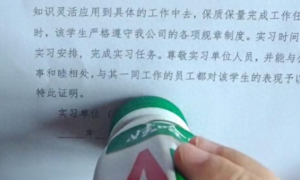契约精神需坚守,但社会也应给合租生育家庭更多包容与支持。
广州白云区一间合租屋内,新生儿的啼哭本该是家庭的喜悦,却成了租赁纠纷的导火索。王女士和丈夫在自如平台合租了一间房,却在生育后被告知“违约”,要求三日内搬离,否则行李将被强制清走。平台方称,合同明确禁止未成年人居住,且因老人频繁出入带孩子,其他租户多次投诉。一方坚称“契约必须遵守”,另一方则质问:“租房合同难道能剥夺生育的权利吗?”这场争论背后,是现代都市生活中法理人情的剧烈碰撞,也是普通劳动者在高昂生活成本下的真实困境。

一纸合同 vs 生育权利:谁的“道理”更硬?
根据媒体报道,自如合同中的条款并非凭空设置,而是源于广州市2022年《住房租赁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出租房人均使用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但同时也留出了例外空间:具有抚养、赡养等特殊关系的同住人可不受该限制。换言之,从政策层面看,王女士夫妇生育孩子并请老人协助照料,并不直接违反地方法规。然而,合同却以“禁止未成年人居住”“年龄限18-40岁”等条款,将生育行为间接排除在外。
许多网友支持平台方,认为“签了合同就要守约”“合租环境不适合养娃”。这种观点强调契约精神的刚性,也折射出都市合租的现实:狭小空间、共享设施、多人共处,任何新增人口都可能打破原有平衡。但另一方面,生育并非主观“违约”,而是基本人权。夫妻二人在租赁后生育,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非恶意破坏规则。更值得注意的是,合同中“禁止40岁以上租客”“拒租老人”等条款日益普遍,甚至衍生出对孕妇的隐性排斥——这些内容是否真正符合法律精神?是否变相构成了年龄和生育歧视?
合租的“囚徒博弈”:没有赢家的生存较量
合租房本质上是都市高房价与低收入之间挤压出的妥协产物。在王女士的事件中,矛盾不仅存在于租客与平台之间,也蔓延至合租者内部。其他租户因婴儿哭闹、老人频繁出入而感到困扰,进而投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反应。但将问题简化为“守约与否”或“谁更占理”,却掩盖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当年轻人被迫选择合租以节省开支,当生育成本与居住压力叠加,社会是否应该提供更多支持而非单纯惩罚?
事实上,这类纠纷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赢家”。房东和平台担心管理成本上升、其他租户流失;新生儿家庭面临突然失去住所的风险;而合租的邻居们也在噪音与拥挤中承受着生活质量下降的代价。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博弈”:每个人都在理性地维护自身利益,却共同陷入了更糟糕的结局。
从“契约冰冷”到“政策温度”:生育友好需要社会加法
要破解这一困境,不能仅靠契约条款的硬性约束,更需要公共政策的柔性介入。广州市政策中之所以留下“特殊情况”例外,正是出于对人性化需求的尊重。然而,现实中许多平台和房东为了规避风险,直接采取“一刀切”拒绝策略,使得本可用于平衡利益的弹性空间形同虚设。
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平台与社会多方协作的“做加法”思路。例如,对符合条件且有婴幼儿的家庭提供租房补贴,减轻其经济压力;对提供长租或接受特殊家庭的房东减免税费,激励其包容性行为;推动平台建立更合理的合租规则,如设置“家庭友好型”合租单元,或提供临时性母婴支持服务。此外,社区公共服务也可以介入——例如通过增设公共托育空间、临时照料服务,分散合租环境中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应当更明确地反对租赁市场中的歧视性条款。年龄限制、生育排斥等内容是否涉嫌违法,需要法律层面的进一步厘清。一个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社会,决不能放任市场规则走向“排斥老人、拒绝孩子”的极端。
结语:居者有其屋,更应居者有其“权”
王女士一家的遭遇,是个体的困境,也是时代的缩影。在“居大不易”的都市中,许多人都在合租、房贷、生计之间艰难平衡。而一个真正进步的社会,应当既能维护契约的严肃性,也能保障生育的正当性,既能尊重房东的权益,也能体恤租客的艰辛。
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是选择“合同至上”还是“生育友好”,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共同构建一个更具支持性的居住生态系统。从政策倾斜到社区支持,从法律完善到市场引导,每一环都可以成为打破困境的突破口。唯有如此,都市的灯火之下,才能容得下一张婴儿床,也留得住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