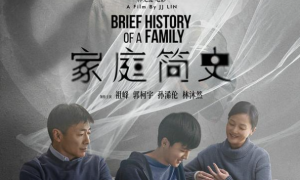一名15岁少年被练拳同学打成重伤二级,施暴者获缓刑并赔偿4万元,但法院未支持伤残赔偿金,家属因孩子未来生计受影响难以接受,目前已提起再审申诉。
2024年3月26日深夜,云南禄丰市广通镇的街道上,15岁的小文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次“爽约”,被同年级的同学马某狠狠击中腹部。更没有人想到,这一拳竟会导致内脏破裂、大出血,最终鉴定为重伤二级和十级伤残。

“我听说过他,但不熟悉,听说他打过其他同学。”小文事后低声说道。他口中的“他”,是曾获省级拳击比赛第二名的马某。那一晚,小文和同伴郭某因未按约定参与所谓的“探险”,与马某等人相遇街头。几句口角之后,拳头落了下来。
“马某可能嫌我们不跟他玩,所以动了手。我有点怕他。”
——小文的这句话里,藏着多少未成年人之间微妙而鲜被察觉的权力压迫?一个“练拳”的少年,一个“获奖”的“冠军”,在校园和街角的小小世界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威慑。
腹痛如绞的小文在旅馆捱到凌晨,直至疼晕过去。次日中午他才被送至诊所,随后紧急转院手术。医生发现他创伤性结肠破裂、肠系膜裂伤、失血性休克……腹腔内动脉血管破裂,生命一度垂危。
手术后,小文活了下来,但身体再也回不到从前。他说:“只要跑得稍快一些,或干一点力气活,就会感到肠子仿佛被撕裂的痛。”而比身体创伤更深的,是心理的剧变。楚雄州人民医院的心理健康报告显示,这个15岁的少年已存在“重度抑郁症状”和“重度焦虑症状”,临床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他甚至会用玻璃划伤自己。
母亲龚女士的声音里是掩不住的心痛与不解:“法院的判决,我作为家长难以接受。”令她难以接受的,是打人者马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三年,其父母赔偿各项经济损失4万元;而法院驳回了他们家关于伤残赔偿金的诉求——尽管小文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尽管那8.7万余元的伤残赔偿金,本可能为他受限的未来提供一丝保障。
“案发后,马某从未给我真诚道歉过,他父亲来医院仅仅是看了一眼。他来看望我,都是派出所民警叫过来的。”小文这句话,让人不禁去想:施暴一方及其家庭,是否真的意识到了那一拳的分量?
而法院的判决,同样引发诸多思考。为何不予支持伤残赔偿金?据律师解释,这并不是地方法院的独有做法,而是源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是否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认定为“物质损失”。
自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来,“两金”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中不再被纳入赔偿范围。法院认为,刑事被告人普遍缺乏偿付能力,支持“两金”可能导致“空判”,引发更多社会问题。这是一种司法政策上的“权宜之计”,但却直接影响了成千上万如小文一样的受害人家庭。
法律条款是冰冷的,但现实疼痛却如此真实。小文的家属在申诉文中写道: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范畴。十级伤残“必然导致其成年后职业选择受限、劳动收入降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赔偿,“实质剥夺了未成年人的未来生存权益”。
2025年9月1日,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向小文出具《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对该案立案审查。这意味着一线新的曙光可能到来。
这起案件,远远不止于一名少年被打伤的个体遭遇。它像一个棱镜,折射出多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议题:未成年人之间的暴力如何预防与问责?司法制度如何更好地回应受害人的真实伤痛?当一个练拳的少年挥出那一拳时,家庭、学校、社会,又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如今,小文的身体仍在恢复,心理仍在挣扎。而马某,则在缓刑期中继续着他的学业。两个少年,本可能拥有平静的交集或毫无交集的人生,却因一瞬间的冲动,被永远地改变了轨迹。
我们期待司法的审查能给出一个更加贴近人本关怀的答案,更期待这样的悲剧能唤起更多对校园暴力、青少年心理、司法救济机制的深入关注。毕竟,每一个少年都值得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而不是在暴力与创伤的阴影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