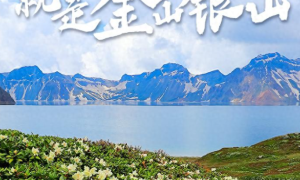吕思勉认为唐太宗只是“中等才能”,其功业更多得益于时代机遇而非个人超凡能力,并指出贞观之治对普通民众的实际改善有限。
中国近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始终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在其遗著《隋唐五代史》中,他直言”太宗不过中材”,与后世”天可汗””千古一帝”的盛誉形成鲜明反差。这一论断背后,不仅涉及对帝王个人能力的评判标准,更折射出吕思勉独特的史观与价值取向。

一、武功质疑: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吕思勉认为,唐太宗的军事成就被严重高估。他指出,太宗平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唯独征高句丽时重蹈隋炀帝覆辙,可见其成功”多徼天幸”。贞观时期突厥分裂、吐蕃未兴的有利地缘环境,使唐朝得以低成本维系边疆稳定。相比之下,汉朝面对匈奴等强敌时需倾举国之力作战,而唐初更多依赖蕃将蕃兵”以夷制夷”。这种差异让吕思勉质疑:”太宗之材武,实未尝过于人。”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对陈霸先的推崇。这位南陈开国君主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以弱势兵力周旋于北齐、西魏等强权之间。吕思勉盛赞其”度量恢廓,知人善任”,认为其军事才能远胜太宗。这种”重逆境奋斗轻顺势成功”的评价标准,凸显了他对个人能力与历史机遇的辩证思考。
二、文治再审视:”贞观之治”的光环与阴影
对于备受推崇的”贞观之治”,吕思勉的质疑更为尖锐。他通过对比《贞观政要》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发现史书对太宗纳谏的记载存在明显修饰痕迹。更关键的是,他从民生角度提出诘问:”贞观四年大蝗灾时,太宗竟需吞蝗示警,可见救灾体系何其脆弱!”
在《中国通史》中,他详细考证了唐初赋役制度:尽管实行租庸调制,但征发徭役仍导致”道路相继,兄去弟还”的惨状。这种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其论断超越传统帝王评价体系——衡量治世的标准不应是疆域大小,而是”小民曾否受其泽”。
三、价值坐标:民本史观下的帝王评判
吕思勉的颠覆性评价,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史学方法论:
- 去道德化分析:反对将帝王”圣君化”,强调制度与环境约束。他认为太宗晚年渐趋奢靡、废立太子等事,暴露出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 比较视野:将唐太宗置于魏晋南北朝至五代十国的长周期中考察,指出其改革力度不及宇文泰、杨坚等过渡性人物。
- 民本立场:在《隋唐五代史》”田制””赋税”等章节中,他反复论证”贞观之治”未能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为安史之乱埋下伏笔。
这种史观与其出身密切相关。作为常州贫寒塾师之子,吕思勉自幼目睹民间疾苦。他在自述中曾言:”读史见百姓流离之状,未尝不掩卷太息。”这种情怀使其著作始终贯穿着对权力异化的警惕,正如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所言:”君主制度下,虽英主亦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四、当代回响:重估传统评价体系的启示
吕思勉的论断在今日仍具启示意义:
- 祛魅历史人物:提醒我们警惕”英雄史观”的片面性,唐太宗的形象实为后世建构的结果。敦煌文献显示,当时民间对”天可汗”的认知远不如后世想象。
- 重构评价维度: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曾指出,唐太宗对外政策实为”危机管理”而非战略规划,与吕思勉的”时势论”形成跨时空呼应。
- 史家责任反思:吕思勉坚持”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这种以史为鉴、心系苍生的治学精神,恰是当代史学亟需传承的品格。
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中,有一段话或许能概括其本意:”论人须观其全,太宗固有足称者,然必谓其超越百代,则非知史之论也。”这种拒绝神化、回归常识的历史观照,或许才是我们重新理解”唐太宗不过中材”这一论断的真正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