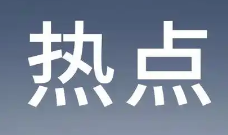武汉七旬老人朱业庭坚守相机维修技艺50余年,凭借精湛手艺在无门店无宣传的情况下,成为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宝藏师傅”。
在数码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一位老人用五十年的时光,让数万台濒临报废的胶片相机重获新生。他的工作室没有招牌,技艺却声名远扬;他从不宣传,却成为无数年轻人追寻的“宝藏师傅”。
在武汉江汉路的一处老居民楼里,藏着一间不起眼的工作室。推开房门,映入眼帘的是满满当当的相机零件、模型机和维修工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戴着眼镜,专注地摆弄着手里的胶片相机。
这里是71岁朱业庭师傅的工作室。没有门面,没有招牌,更没有网络宣传,仅凭口耳相传,这位修了50余年相机的老师傅,成为了当下年轻人争相寻访的“相机爷爷”。
01 藏在阁楼里的相机医院
穿过江汉路一家银饰店,右转登上老式楼梯,才能找到朱师傅这间约30平方米的工作室。工作台上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精密工具,墙壁上挂满了各式旧相机,老式储物柜里分门别类地收纳着成千上万的相机零件。
这不像商业店铺,更像是一间充满历史感的私人博物馆。每一台相机、每一个零件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朱师傅就坐在这片天地中,日复一日地让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老伙计”重焕新生。
“修相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朱师傅笑着说道,手中的螺丝刀却丝毫未停。尽管已经71岁高龄,他每天仍能修复3-4台胶片相机。简单的故障40分钟就能解决,收费仅200元;即便是高端相机的复杂维修,他也只根据难度和配件成本收取700到上千元的费用。
02 半个世纪的技艺沉淀
朱师傅的修相机生涯始于16岁。“我父亲原来是修钟表的,后来改修相机。”在父亲的影响下,他走上了这条道路,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他依然记得自己修复的第一台相机——国产海鸥牌。从机械相机到数码相机,再到如今重新回潮的胶片机,他见证了相机产业的整个变迁史。
“武汉现在修相机的师傅里,有不少都是我带出来的徒弟。”朱师傅不无自豪地说,他带过的徒弟少说也有六七十个。但问及手艺传承,他的眼神却黯淡下来:“已经失传了。”他曾花一年时间教导儿子,但年轻人始终无法静心钻研这门技艺。
03 复古浪潮中的定海神针
近年来,CCD相机的翻红、胶片相机的回潮,以及上百元一张的撕拉片席卷社交媒体,让复古相机再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这股热潮中,朱师傅这样技艺精湛的老师傅成了备受追捧的“宝藏”。
“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来到我这里修胶片机的多是年轻人从各个社交媒体平台自己找过来的。”朱师傅说。一位曾来修过相机的年轻人评价道:“之前找别人修要600元,而朱师傅只需200元,而且修得挺好。老师傅没有乱喊价。”
修复胶片相机是门精细活。需要通过操作判断故障源,依序拆卸,清洁保养机械与光学部件,更换老化海绵、光圈叶片等易损件,最后校准快门速度与测光精度。这些繁琐的流程,朱师傅做了半个世纪,依然保持着80%的成功率。
04 手艺人的执着与坚守
虽然年纪大了,做事速度不如从前,但朱师傅的手艺依然精湛。“年轻时拆卸零件必须按顺序整齐摆放,而如今即便配件摆放得略显凌乱,我也依然能准确无误地组装起来。哪个螺丝应该上到什么位置,我在心中都有一笔账。”
当相机缺配件时,他会在二手平台上淘买旧机,拆卸可用零件。在他的家中,还留有两个抽屉的配件机,这些都是他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源。
相比数码相机,朱师傅更钟情于胶片机的修复。“数码相机都是模块式的,坏了什么就换什么。”但实际上,由于专用配件难以获取,数码相机的维修有时需要亲手焊接、重建电路,反而比机械相机更考验耐心与应变能力。
05 手艺与人生的融合
“哪怕我休息一天,至少也会接到四五个来找我修相机的电话。”朱师傅说。偶尔带妻子出去旅游,也总惦记着那些待修的相机,急着赶回家。“免得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了。”他笑着说,眼神里满是热爱与执着。
在这间小小的工作室里,朱师傅见证了相机产业的兴衰更迭,也见证了无数人生的珍贵时刻。那些被送来的相机,大多承载着主人特殊的情感记忆——或许是记录孩子成长的第一台相机,或许是陪伴多年的旅行伙伴,又或许是父辈留下的珍贵遗物。
“修相机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责任。”朱师傅说,“每次把修好的相机交还到主人手中,看到他们欣喜的表情,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值了。”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朱业庭师傅用半个世纪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匠人精神。他的工作室没有华丽的装潢,没有炫目的广告,有的只是对手艺的尊重和对品质的执着。
当问及何时退休时,朱师傅笑了笑,目光再次回到手中的相机上:“只要眼睛还看得见,手还稳得住,我就会一直修下去。这些老相机等着我给它们新的生命呢。”
在这个数码产品更新换代飞快的时代,朱师傅和他的工作室仿佛一座孤岛,守护着那些即将被遗忘的技艺与记忆。而每一次快门的重新响起,都是对这份坚守最动人的回应。